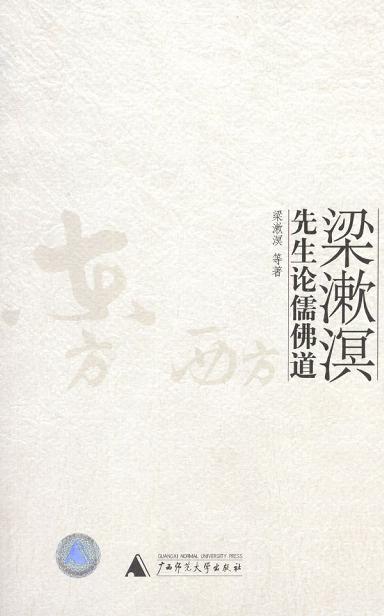
作者: 梁漱溟
出版社: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年: 2004-03
页数: 264
定价: 19.80
装帧: 平装
ISBN: 9787563343324
孔子学说之重光
孔子的学问就是要自己了解自己,自己对自己有办法;而不是要自己不了解自己,自己对自己没办法。
“不惑、耳顺、从心所欲不逾矩”这些我们隐约看出,他心里很通达,自己很有办法,自己不跟自己打架。孔子毕生致力于就在让自己生活顺适通达,嘹亮清楚。
“不迁怒,不贰过”。
《中国民族自救运动之最后觉悟》:中国文化和印度文化有其共同的特点,就是要人的智慧不单向外用,而回返到自家生命上来,使生命成了智慧的,而非智慧为役于生命。
中西学术之不同
凡真学问家,必皆有其根本观念,有其到处运用之方法,或到处运用的眼光;否则便不足以称为学问家。
在儒家是用全副力量求能了解自己的心理,如所谓反省等。道家则是要求能了解自己的生理,其主要的功夫是静坐,静坐就是收视返听,不用眼看耳听外面,而看听内里——看听乃是譬喻,真意指了解认识。
总之,东西是两条不同的路:一面的根本方法与眼光是静的、科学的、数学化的、可分的。一面的根本方法与眼光是动的、玄学的、正在运行中不可分的。
东方学术概观
第一章 结论
所谓人类智慧者非他,人心内蕴之自觉是已。凡用心在某一事物或某一问题者运用感官探索之时,必留有印象于衷怀自觉中,先后多次较量,乃悟得其相关规律,从而步步深入焉。然一人经验有限,更赖彼此交流,先后传递修正,有小道而蔚成大观。
学术分类归入三类:第一问题者,人对物的问题也。此问题我说为人生第一问题。在第一问题之下,从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推进着社会向前发展,这就是马克思阐述的社会发展史。社会发展端在分工,是有阶级分化,而终归于消泯阶级的社会主义社会。人类生活便从第一问题传入性质不同的第二问题。第二问题者,人对人的问题也。其主要问题在人与人如何得以和衷共济,彼此无忤。在第二问题愈来愈得到解决之下,人类生活自将大不同于今天纷争斗殴的世界,殆吾古人所称大同之世、太平之世者。正在如此生活中,客观条件更无任何问题存在,人们乃始于烦恼在自身,初不在外,大有觉悟认识,而求解脱此生来不自由之生命焉。人生从第二问题于是转入第三问题,而出世之学将为人所讲求。
性质上属于第二期的儒家之学,属于第三期的佛家之学,介于第二期与第三期之间的中国道家之学和印度的瑜伽学。
第二章 儒者孔门之学
宗教总是教人信从他们的教诫,而孔子却教人认真地自觉地信自己而行事。孔子与宗教的分水岭在此。
人心通常总是向外照顾寻求如何有利于自身生活的,其行事通常说为有意识。而意识之原义即自觉。二者似乎分不开。但有必要注意其分别:从其对外活动则曰意识;从其内蕴昭明非以对外者则曰自觉。人的意识往往不足恃,不可信。其落于不足恃不可信之故有二:
一者,向外活动时,则内蕴之明不足。——“自觉与心静是分不开的。必有自觉于衷,其可谓之心静;唯此心之静也,斯有自觉于衷焉。”
二者,向外活动进退取舍之间决于利害得失的计较而非从乎无私的感情。——“具此无私的感情是人类之所以伟大;而人心有自觉则为此无私的感情之所寄焉。”
自觉能动性为人类的特征,表现出至高无上的主动精神。但人们却可怜地大抵生活在被动中:被牵引,被诱惑,被胁迫,被强制……如是种种皆身之为累而心不能超然物外也。自觉能动性是无时不有的,无奈人要活命先于一切,不免易失而难存。所以良知既是人人现有的,却又往往迷失而难见,不是现成的事情。孔门之学就是要此心常在常明,以致愈来愈明的那种学问功夫。
识得是根本,不失是功夫。
第三章 道家之学
儒家为学本于人心,趋向在此心之开朗以达于人生实践上之自主、自如。道家为学所重在人身,趋向在此身之通灵而造乎其运用自如之境。
身内饮食消化、血液循环,等等一切无时不在运行中,各有司其事者,因而亦称自主神经。其特征在机械化,仿佛亡失自觉(吾人意识所不及)。道家功夫一言以蔽之,即通过大脑恢复其自觉性能是已。能自觉,便能自主而自如。
此学介于世间法、出世间法之间。因其对于人世间显示消极,近乎出世矣,而仍处在生灭迁流中,终未超出来,属于佛家所谓有为法,非所谓无为无漏者。无为无漏的无为法唯于佛家见之。
第四章 佛家之学
佛家三法印:
- 诸行无常(诸行指一切生灭流转的世间有为法而言,故是转变无常的)。
- 诸法无我(诸法兼有为法和无为法而言,“我”在凡夫执念中则有恒一主宰之义。不论在有为法在无为法同是无“我”可得的)。
- 涅盘寂静(涅槃之义为圆寂,为解脱,即谓从生命解放出来,不再沉沦在生死轮回中)。
起惑、造业、受苦是佛家的人生观,起惑之惑指众生的我执,无我可得而强执着之,故是惑也。佛教初(小乘)终(大乘)一致地在破我执。破我执,即一口说尽了全部佛法。
另有大乘教的法印:一切法平等的实相。
所谓生活就是吸收和排泄,时时在自我更新之中。一旦不进不出,新陈代谢停止了便是死亡。一切生命现象全基于有“自我”见,然而“自我”却是忘情而已。赓续生灭的世间法原于众生我执而来,一切不过是假象。忘情执着则有,涣然冰释则无。
佛说“无始无明”,即指众生我执之迷误说。一切分别执着从此滋蔓纷纭,漫衍无穷。世间生灭迁流不驻,便是这样积重难返,弄假成真的一回事。脱出迷途,未尝不可得之一悟,如迷东为西者,东西不曾为之易位,一时有觉,天清地宁。然佛之设教则循从两步以利开导。初步指出色、受、想、行、识五蕴为人们执著有我之所从来。常一主宰之我是没有的,所有者不外此五蕴而已。破我执至此,犹存五蕴生灭、染净、增减之分别,亦即世间与出世间之分别。此关不透破,不行,必深入地明了五蕴空幻(《般若心经》云:“行深般若波罗密多时,照见五蕴皆空。”)。既净烦恼障,更净所知障,达于一切法平等平等之实相。倒翻初教,乃得究竟涅槃。———实则佛法不离初教而有,翻乎不翻,相反适以相成。
根本之学在六波罗密(一布施,二持戒,三忍辱,四精进,五禅定,六般若智慧),从世间生命解放出来。
大乘佛教由是歧为性、相两宗派。唯识之学则出于瑜伽师静中之谛察生命活动;此虽非以外物为对象,而其务于分析辨察则又类似科学家之所为。因其分析名相,称为相宗,与般若空一切相者若为对立。性宗在前,相宗在后,释迦身逝一千余年在印度本土大乘佛教要即歧为此两大宗派。
佛家之学,盖从世间迷妄生命中解放之学也。法相唯识则是对于如此生命之剖析说明;其能为此剖析说明者,则修瑜伽功夫之瑜伽师。瑜伽即是禅定,为六波罗密之一。修六波罗密,从静定中返照而得生命之一切,乃出以指说于为此学者。
第五章 论学术内涵及其分类(上)
人生实有三大不同之问题:
- 人对物问题。以人必资于物以生活,面前自然界种种乃首先为其经验对象,从而成就得种种知识以至高深学术。
- 人对人的问题。人在从事生产和生活中,彼此离开不得,是有群居之大小集体组织(家庭、社会等),其间如何乃得相安相处,自是一大问题不同于前者。于此,正自有其不同于前的一种学问在。
- 人对自己的问题。人对自己并非不发生问题的。不过当其困扰于前两大问题时,此一问题不显现耳。外在问题解决了(共产社会进达高度时),人便发现烦恼非从外来,而有以解脱此生来不自由的生命,体现乎自由,这是种彻究宇宙生命的学问。
儒、佛、道三家之学均贵践履实修,各有其当真解决的实在问题,非徒口耳三寸之间的事。不掌握此点,不足以言三家之学。
第六章 论学术内涵及其分类(下)
我今就古今东西学术试分为四大类别如下:
一曰:科学技术
二曰:哲学思想
三曰:文学艺术
四曰:修持涵养———简称修养
儒佛异同论
儒家从不离开人来说话,其立脚点是人的立脚点,说来说去总还归结到人身上,不在其外。佛家反之,他站在远高于人的立场,总是超开人来说话,更不复归结到人身上———归结到成佛。前者属世间法,后者则出世间法,其不同彰彰也。
然儒佛固又相通焉。其所以卒必相通者有二:
- 两家为说不同,然其为对人而说话则一也(佛说话的对象或不止于人,但对人仍是其主要的。)
- 两家为说不同,然其所说内容为自己生命上一种修养的学问则一也。其学不属自然科学,不属社会科学,亦非西洋古代所云“爱智”的哲学,亦非文艺之类,而同是生命上自己向内用功进修提高的一种学问。
佛法与世间
- 一般人以为佛法只注意生死问题,如所云“生死事大,无常迅速”,似志在超出轮回,不受后有,而忽视现实世间生活者,非也。
- 佛法并不否认人生价值,并没有脱离世间生活的说法。相反地,要投身于世间,渗透于世间,而求世间本质上的变革,即从观行而得转依,以转依代解脱。
- 大乘的涅槃有殊于小乘的涅槃,不可混同。大乘佛法在发起善法欲,即是净化人生的愿望,累积功德,逐渐解决矛盾,以开出转依的途径,能转化世间即是出世。
《礼记·大学篇》伍严两家解说合印叙
- 儒家求仁之学,不外自勉于实践人之所以为人者;
- “仁,人心也”,人之所以为人者独在此心,其异于禽兽物类者几希;
- 心有一息之懈便流于不仁(粗言之,内失其清明,外失其和厚),亦即失其所以为人;
- 是故求仁之学即在自识其本心,而兢兢业业葆任勿失,以应物理事;
- 然而人自识其本心———亦即识仁———却甚非易易。
两先生功夫虽若不同哉,然正自有其共同一致者在。此可以两言括之:
- 心不可求也,则以不求求之;
- 近道自然合道。
《礼记·大学篇》伍氏学说综述
一、明明德
明德即本心,亦曰“性体”或“本体”,其在阳明王子则所谓“良知”也。明德即人的本心,亦曰“性体”,既非可见可捉之物,便只能从它这些作用上见之。凡此内心不失其明者皆明德也。
如何不失其明德之明,或如何得以复其明德之明,于是为必要。这就有“明明德”之说了。《大学》一书之所为作,凡为此而已。
二、近道
道指本体,即性体,即明德;近道指功夫,即可以大入道或合于道者。“大学之道,在明明德。”通观《大学》全篇,其讲近道者(自“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以下均是)宁着重过其讲道。盖唯其讲近道,乃正所以讲如何得以明明德也。
三、格物致知(上)
格物之“物”即上文“物有本末”之“物”;致知之“知”即上文“知所先后”之“知”。我们只须把上文———
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
和它所紧接之下文———
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
一气贯通来领取其意旨就好了,这中间所谓格物致知讵有新奇涵义,不外能够通达了这所有一连串的本末先后关系,而归结得“修身为本”一法则或信念上而已。近道之提出必到此乃落实也。
伍先生指点出《大学》书文上“物”字凡三见:(一)物有本末;(二)致知在格物;(三)物格而后知至。
没有一处不是关合到本末先后说的。因此,我们不应离开本末先后问题泛泛去说“物”。———那样的“物”和《大学》这里无干涉。
小结是:照朱王两家那样解《大学》,《大学》功夫就在格物致知上做。但他们所认为是功夫的格物致知,在伍氏学说综述伍先生却认为那只是功夫的前提。因为格物致知只是认识得“修身为本”这一法则,产生了“修身为本”这一信念,衷心不敢或违而已。由此一认识和信念乃引归到诚意慎独;功夫全在诚意慎独上做。
四、格物致知(下)
作为功夫之前提的这个敬,在朱子亦何尝不意识到其必要。所可惜的,他却没有示人以如何去收敛身心,怎样便得尽扫杂虑,而遽索光明洞达之效果于一般学人。
伍先生讲“格物致知”之怎样导引人心向里,总分做两层,亦曰“两关”:第一,责己,不责人(“躬自厚而薄责于人”),是为 “人己关”;第二,只知有内,不知有外(外面一切俱收照在内心),是为 “内外关”。透过这两层关口,则神不外驰,心自精明。当然,这亦是要由生而熟,慢慢来的。却是期之以渐,朱子说的“光明洞达”不难驯致。
伍先生强调格致只不过一认识、一信念而非功夫;功夫要在诚意慎独上做。然这认识和信念却与功夫实践其势相联,而互为因果的。即是:由认识信念引到功夫实践;还由功夫实践使得认识真切而增强其信念。功夫有生有熟,有浅有深,认识和信念随之亦有进境不同。前所说的两关应包括格、致、诚而理会之。
五、修身为本
从格物致知得来的只是“修身为本”一句话,更无其他。舍此他求(如朱子、阳明),皆不免求之太深,用心太过。修身为本,不唯是《大学》一书要旨之所在,抑且为儒家一根本思想,普见于其所谓“四书”者:《大学》、《中庸》、《论语》、《孟子》。
“修身为本”意旨者多有其例。其中有些语意相同,甚且文字亦略同的。例如《论语》上“躬自厚而薄责于人,则远怨矣”;在《中庸》上则有“正己而不求于人,则无怨”。《中庸》上“射有似乎君子,失诸正鹄,反求诸其身”;其在《孟子》上则为“射者正己而后发,发而不中,不怨胜己者,反求诸己而已矣”。
伍先生时常称引《中庸》上的下列一段书文:
子曰:“道不远人,人之为道而远人,不可以为道。《诗》云:‘伐柯伐柯,其则不远。’执柯以伐柯,睨而视之,犹以为远。故君子以人治人,改而止。忠恕违道不远,施诸己而不愿,亦勿施于人。”
六、诚意慎独(上)
所谓诚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恶恶臭,如好好色,此之谓自慊。故君子必慎其独。
《中庸》上说“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在天,什么事情就是什么事情,一点不会有假的。所以天就是诚。不诚,只在人方有之。人之不诚(做假),是他想要背天。但其结果,还是背不了;是什么,还(现出来)是什么。所以“诚之为贵”。说“诚之”,就是要诚意。“诚之者,人之道也”,就是:人之道在必诚其意。
凡有所受,必自身而通乎心;凡有所施,必自心而通乎身。身心联通乃有活动,两方面缺一不可,而意即萌茁于其联通之上。一般说来,身心之间时时往复联通,时时有意,时时有活动。
我举此事例(失眠),希望人们反躬来认识两点:
- 一点是日常生活中自己意念之动,是不是时常落于被动而不自觉?
- 一点是自己的身和心时常是合一的呢,抑或常是不免分着的?
前既言之:意者,意向。既曰“意向”矣,天然只许有一个,岂容有二?而从上研究的结论,所说身心分者其实恰便是意向不一。———意向不成其为意向,正是意不诚。于此即得意不诚之确解。
七、诚意慎独(中)
意者心之所发。心为主宰义;意即其代表。若其意向不一,则所以为主宰者安在?因此,意向不一者,心失其为心矣。是何为而然耶?人在环境中,或受或施,意之萌茁也,必在身心联通之上。于此际也,身一面(兼本能习惯而言)势力或强逾乎心,则意偏从身来———其动向本于身———而心隐昧不见。夫身所蓄积之动势种种非一也,有好色之本能,复有顾全声名之习惯;既贪货利,又畏刑罚;见义不为,临阵无勇,瞬息之间,意念再变;如之何其意向得一而不贰耶?
生物之一生,莫不为其个体生存、种族繁衍而尽悴。人为生物之一,夫何能有独外。故食色之于人,动势最强,好难克制;而克制之最难者又莫如怒。盖禽兽争食争色,斗其常也;然唯斗而胜者得在天演淘汰中保存繁衍,是必其忿然一往不恤不顾者。演进至于人,犹存本色焉。所以昔人曾说“人情之易发而难制者惟怒为甚”(宋儒大程子语)。人临此境,不正是所谓不由自主,亦就见出对自己之无办法了吗?
总结说:从后一点身心分合问题的研究,让我们明白了所谓身心分着,实际上就是意向不一。而研究前一点———意念出于被动而不自觉———得到的认识,则让我们明白了后一点———身心常不免分着———之所从来。那就是:意向所以常不一者,正不外意之萌茁常偏从身来而心则无力也。说得重些,便是:只见有身,不见有心。
请读者参看《〈礼记·大学篇〉伍严两家解说合印叙》的一段话:
在吾人生命中恒必有一部分转入机械化(惯常若固定然),而后其心乃得有自由活动之余裕。此在个体则本能与习惯,其在社会则组织与礼制,皆是也,是皆人类生命活动之必资藉,非必障蔽乎心也。然而凡可以为资藉者皆可转而为障碍;此一定之理。
心不能用之,则转而为其所用矣。其辨只在孰为主,孰为客耳。其辨甚微,而机转甚妙,心有一息之懈,而主客顿易其位焉。
心本来是主,而近乎机械化的那部分本来是工具,然而每每却主客颠倒。一息之懈,不是极其容易的吗?所以“只见有身,不见有心”乃极其普遍的事情了。
“意向不一而总是在向着外”,其最可见者莫如其能忙,不能闲。人一闲着无事干,便觉无聊,总要寻些事情来消遣时光。打牌,下棋,看戏,听故事,谈闲话,吃零食⋯⋯如是种种不一;而一言以蔽之,总不过是寻些外面刺激(得失、胜负、喜怒、悲欢、酸甜、苦辣)来刺激身体神经。身体疲乏了,倒下去睡。睡起来后,又是要这样或那样忙去,总是闲不得。一时无刺激,便感到茫无着落。俗说“如猢狲失树”,古人说“逐物不返”皆谓此。
心(完整的精神)是照顾全面的;发而为意,若无偏欹,本无疏失。心懈无主,意偏外走,便有疏忽不周。这便是自欺了。“自欺者有所亏缺之谓也。”(伍先生语)若随即自觉,毋外走去,则当下仍然是整个精神,便意无不诚。然而此心久已习惯于外放者,夫岂易言哉!
一切行事以意为其先导。说心必当放在事上,即是功夫要在意上做。如前文说过的:自然而整个的敬,则明德之用渐启而有微明。诚意功夫即以此作根基。“所谓诚其意者,毋自欺也。”意既是一向容易自欺而不自觉的,今有微明便会有所觉察,于是乃得有毋自欺之可言。微明不是虚见,而是觉痛、觉痒、有好、有恶的。“毋自欺”之“毋”的力量从这里来(毋是决绝之词)。
痛痒、好恶是人的生命天然自有的,且时时都在有的;而是非善恶之辨正不离乎好恶。阳明有言“只好恶就尽了是非”是也。《大学》“如恶恶臭,如好好色”之喻,大正谓觉知自欺的觉中天然有恶在,自能毋而去之。若其觉而不能恶,恶而不能毋者,是其好恶不明不强,濒于心死也。是必有所牵,有所蔽,精神分散而不集中,生命表现无力也。其病都在身心不一。身心果合一,精神便是整个的。整个精神在当下,好恶痛痒自明强。
照伍先生看:《大学》诚意功夫正不外是要一个人恢复其身心合一的本然(或云正常)而已。其功夫全要在意上做,即是刻刻慎独毋自欺。这是《大学》彻始彻终的功夫,对于前者格物致知使身心开始合拢的第一步而说,亦可云第二步。
八、诚意慎独(下)
诚意功夫怎样做?曰:是必在慎其独。慎即留心(或当心)之谓;独即指自己。合而言之,便是留心自己。
伍先生之示学者云:信得修身为本而后精神回到身上来,此时于意念之萌着一“慎”字,便已够了;下面一个“独”字只是补充。然以“独”配着“慎”来说,却大有好处:
第一,在独处(人不及见)之时,在独念(人不及知)之上去慎,这慎是真慎,不是什么顾虑夹杂的慎。这方是古人为己之学。好是自好———好我之所好;恶是自恶———恶我之所恶;欺是自欺(歉仄),慊是自慊(快足);什么都是自己事,原与人不相干。人知与不知都不去管。一切为己,一切求诸己。
按:先生又尝云“搞通这思想(指《大学》中的《格致》、《诚意》两章),便生信仰。这信仰是信仰自己的。
第二,独中用功,有制于几先的意思;即阳明先生所说“防于未萌之先,克于方萌之际”者是也。这样,较易为力,功夫亦才快。
第三,昔贤(大程子)云“圣人千言万语只是欲人将已放之心约之使反复入身来,自能寻向上去”。《大学》从格物致知到诚意既罔非此旨,这里提出一“独”字,更使你精神有立时集中归一之效。
从格物致知以至诚意慎独,总不过“留心自己”一句话,然其中却大有浅深粗细等差不同:第一步留心于身(一切言动行事);第二步留心于隐微之意(言动行事的先导);第三步身心合一慢慢惯熟了,才迫近“几”。(见后文)
《格致》章讲的本末先后,《诚意》章讲的内外隐显,不过将整个人生(括举自然和社会环境在内)之实况分作两层来说它:本末先后指示出个人与远近社会间如何相关系;内外隐显指出心、身、事之间如何相关系。此中,身为本末之枢纽,意为内外之枢纽。伍先生尝云“慎从本末来,独从内外来”。
关于“人生而静,天之性也”那一段理论,我在《人心与人生》中有讲明,这里从省。但可指出:此“天理”是说人类生命(兼个体群体而言)上天然自有之理。一切天然自有之理———物理学上的物理在内———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者皆天理也,不可违也;违之即错误,只有失败。“人欲”则指人们含有自欺成分的意向。天理、人欲是互为消长的。人欲消尽,则天理流行。古人所云“减尽便没事”者指此。
濂溪周子《通书》有“诚”、“神”、“几”的话,其原文云“寂然不动者,诚也;感而遂通者,神也;动而未形,有无之间者,几也”。大约合天即诚,天理流行便神;其“几”字本于《易经》“几者,动之微,吉凶之先见者也”而来,大约是指天然萌动的意。伍先生曾说,身心合一慢慢惯熟了才迫近“几”(见上文),亦即指此。先生又曾说,“慎”与“几”两字是有密切关系的;“慎”是就功夫言之,“几”则从本体一面而言其用也。看来,诚、神、几,只是一事。
九、功夫次第进境
《诗》云:“瞻彼淇澳,黃竹猗猗。有斐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瑟兮黅兮,赫兮喧兮。有斐君子,终不可喧兮!”如切如磋者,道学也。如琢如磨者,自修也。瑟兮黅兮者,恂慄也。赫兮喧兮者,威仪也。有斐君子,终不可喧兮者,道盛德至善,民之不能忘也。
如伍先生所讲解,此中具有六个层次,即:(一)道学(二)自修(三)恂慄(四)威仪(五)盛德(六)至善
又说为三个阶段:道学和自修为士的阶段;恂慄和威仪为贤的阶段;盛德和至善为圣的阶段。
一般人非遇到挫折,总不免粗心浮气,精神恍惚,其知也不明,其行也不力。一慎,才显出知来;再慎,才能行起来。故好学、力行原属慎独功夫天然不可少的内容,且应是彻始彻终一贯到底的事。其特著见于第一阶段者,功夫方生而未熟,未能行所无事也。及其既熟(第二阶段以次),则不必以为言而自在其中。
关于第二阶段且容后说。伍先生一生谈学而不著书。其谈学也,往往反复叮咛,不厌其烦。1951年4月21日于《大学》全篇解说既竟之后,又尝为吾等告语云云,于慎独功夫重复有所申明,兹特转述之。
先生云:前时讲说诚意慎独,归拢来不外以下四点意思:
- 精神较为是整个的(不分驰)。
- 功夫是反之的。
- 功夫做起来,一方面自觉不昧(毋自欺),一方面又在了解事物。
- 要约言之:留心自己———从留心视听言动以至留心于意。
今再次分别有所申说如下:
- 功夫在当下。———精神收回来只在眼前用,仿佛整个在当下的样子。
- 功夫只在方向上,方向是反的。———不为外物所牵引,不重在责备别人就是反。功夫用力只在这反的方向上,不是方向之外还有用力处。反是“勿忘”(见《孟子》),若更有什么用力,却是“助长”(见《孟子》)了。
- 功夫是合内外之道的。———一慎字具有两面功用;于内则毋自欺,于外则切磋琢磨,好学力行。尝亦用“好善”二字来代表它,即要如舜之“好问好察”,“取诸人以为善”,“明于庶物,察于人伦”那样。盖闲邪和存诚是同时的事。譬如擦镜然。反就是擦,擦就明。———擦去尘障,便自明照于事物。从这一面说是进德,同时那一面就是修业,故曰“合内外之道”。
- 功夫是在有无之间。———此乃是说用功夫的情况宜不滞于有,不沦于无。《大学》之说正心也,“有所忿懥,则不得其正;有所恐惧,则不得其正;有所好乐,则不得其正;有所忧患,则不得其正”。夫忿、惧、忧、乐四者皆人情之所不能无也,然一落于“有所”云云则着矣,滞矣,心失其正矣。盖凡此皆交物而引,心往外走之现象也。吾人从事慎独功夫,一慎便打断往外,而有所者立变为无所。无所,斯不滞于有;但既是慎焉,正亦不沦于无。用功必须灵活,若慎独而有所慎,斯失之矣。
续述第二阶段。功夫进境到第二阶段,涵括恂慄、威仪两层次。先生以为这应是功夫日密,臻于纯熟,总不间断了。恂慄言其里,即形容其内一面之恒一不懈,正是《中庸》上所谓“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者。威仪言其表,即由心而形著于身;身心内外合一,有如《礼记》所云“和顺积中而英华发外”,《孟子》所云“睟然见于面,盎于背,施于四体,四体不言而喻”者。
第三阶段涵有盛德、至善两层,已是圣人境界,不必要多所臆测,伍先生不多谈它。
十、余 论
这里有先生归纳《大学》全文旨趣的十六句话:
把截诸路头 赶归这一处
又塞那渗漏 更无何处去
当下活泼地 好学力行哉
日新又日新 明明孝弟慈
絜矩一原理 人财两原则
好恶必同民 去举宜远亟
增节复平均 义利严分别
好古敏以求 先难而后获
“把截诸路头,赶归这一处”,是说修身为本。许多路头如何都被把截了呢?审知身、家、国、天下间的本末先后之理,舍致力修身而外,其他的路都通不去故也。此理为天然自有之理,不问你知与不知,不容有违。违之,必定失败无效;顺之而行,则得则安。譬如责人则离则疏,责己则亲则合,感应不爽,若相默喻于无形。明白而有志的人便不要再枉费心力于不通之路,一意于反己修身。
“又塞那渗漏,更无何处去”,是说必慎其独。精神收回到身上来,总不离本了,还有个内外隐显之理在。要知道:诚于中,形于外;无隐微之不显现。此亦天然自有二一三之理,分毫不爽。你不责人而责己了;是真责,是假责?这里不真,便是自欺欺人,而欺是欺不了的。除了必诚其意,必慎其独,还向何处去?
“当下活泼地,好学力行哉”,这两句实涵有上文曾经讲过的那四点意思在内。四点意思亦尝被简化为四句如下:
重点在当下 方向即用力
其道合内外 功夫有无间
此可回看上文,不再加解说。但要指出“好学力行哉”自是相应于“其道合内外”的第三点,而“当下活泼地”却实结合了第一、第二、第四那三点意思在一起。我们必须好好理会这联结上面四句的紧切用功之后而立即出之以欣乐神情的两句话。
原来紧切用功是好的,却怕着手过重,不得其方。功夫必结合了第一、第二、第四各点在内才得。此即是说:精神集于当下,心常现在(第一),方向自是反的,如此亦就行了(第二),勿格外用力,有失自然灵活(第四)。不有此结合,那“当下活泼地”的话是说不出来的。随后一句“好学力行哉”,四点完足,而欣乐神情毕见。四点原从一事(具体功夫)的剖析而来;剖析是为了学者便于去体会和检查的。
八句之末两句“日新又日新,明明孝弟慈”;这却是引用了《大学》原文来的。慎独功夫本于人人固有之明德,谁都能作;即在不晓得做功夫的人亦未尝不偶一有之(甚且可以屡屡有之不自知耳)。学者之所贵,只在其能继续绵密而已。慎即心在,外而视明听聪,内而自觉不昧,斯之谓心正。继续慎下去,视听言动一一不苟(一一毋自欺),即是身修。正心、修身功夫都在慎独上,非别有功夫也。齐家在修其身,亦非别有齐家的功夫。推下去,治国、平天下总都一样。孔子曾说“修己以敬”,“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修己以安百姓,尧舜其犹病诸”;岂不可见。慎独即所以修己,原是贯彻到大小事情而无二的功夫。慎即明,继续慎即继续明。明明德即日新其德。“日新又日新”的话,就从这里来。孝、弟、慈则是处家、处国、处天下,对不同的人的不同德行表现,而其一出于明德之明则无不同。所以说“明明孝弟慈”也。
“修身为本”、“必慎其独”